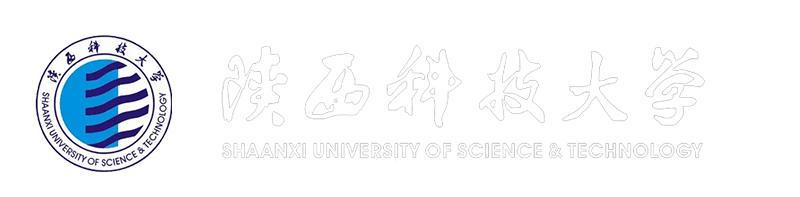编者按: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实施“文化建设浸润行动”,明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,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、革命文化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。“三创两迁”大学精神镌刻着陕科大“姓党、爱国、为人民”红色基因,更是一代代陕科大人取之不竭、赓续不息的文化宝库。新学期伊始,党委宣传部、离退处走访了在“三创两迁”历程中留下光辉足迹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工,听老同志讲述那些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,为书写“教育强国,科大何为”答卷、走好“复兴期”开局起步的后来人加油鼓劲。

周令华:1936年生,浙江黄岩人,教授。1956年9月至1961年7月在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学习,1961年8月至1961年12月在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工作,1961年12月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任教,1970随学校西迁至陕西咸阳,在西北轻工业学院机械系任教。曾任机械系副主任,1997年退休,现定居陕西咸阳。

张淑娟:1941年生,上海市人,副教授,西北轻工业学院食品学科创始人之一。1959年9月至1963年7月就读于北京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。1963年7月至1970年4月在北京酒精厂工作。1970年时参与北京轻工业学院西迁至咸阳,先后在皮革系、食品系任教,2002年退休,现定居陕西咸阳。
北京岁月:迤逦青春的如歌行板
我1959年从上海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,是北京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首届学生。当时欧美国家关于发酵的研究已经很专业了,有专门的“生物工程”学科,主要偏重微生物生理与代谢、单一菌种的培养技术以及基因重组技术的新兴领域,而苏联相关学科叫做“发酵工艺”,主要偏重群体发酵与混合培养、传统发酵工艺等。我们国家的研究起步晚、发展落后,课程设置基本是学习苏联的,大部分教材也都是翻译苏联的,主要从实用角度出发,从事人民生活需要的酿酒、医药领域的研究。当时全国各地兴建国营酒厂、药厂,轻工部希望学校能迅速培养这类企业需要的人才。
我们系的创始人、系主任是金培松先生。他是浙江金华人,1931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化学系,1934年任民国政府中央工业实验所酿造试验室主任,兼任四川教育学院和重庆大学教授。1944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,归国后任中央工业试验所发酵室主任,对麻胶发酵菌、右旋糖肝(人造代血浆)、柠檬酸发酵研究和中间工厂试验以及选育金霉素、链霉素,都获突出成就。抗战期间,南京遭到日寇空袭,他不顾得个人及家庭安危,将面临轰炸的实验室内数百株菌种装入两只大皮箱,一路护送到大后方重庆。1954年,他研究的“发酵法制造葡萄糖酸钙”研制成功,每年生产几百吨,为我国节省几百万元外汇。新中国成立后,因科研成绩显著,他数次受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,多次参加全国科技规划会议,并且多次受到周恩来、陈毅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。
在我们眼里,金老师知识渊博、精益求精,全身心投入在菌种的培养上,当时学校没有保温箱,金老师就自己做了一个像子弹带一样的布袋子缠在身上,里面放满试管,用他的体温培养菌种,后来听李光模老师说,他还专门到轻工部请求为学校配置一台培养菌种的保温箱,当时国内没有生产,轻工部就专门批经费从日本采购回一台。
我们系当时师资是比较雄厚的,教师、实验员的人数和学生人数差不多一样了,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曾准、夏淑兰、姚国雄等,开的课也多,发酵专业基础课就有七八门,化学就开了《无机化学》《有机化学》《物理化学》《生物化学》《分析化学》等。听金老师讲课让人“头疼”,因为他的普通话“浙江味”重,还夹杂着很多英语和拉丁语,听完他的课,总是需要助教夏淑兰老师再“翻译”一遍。
朱康院长特别关心大家的生活。当时赶上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几年,我们南方人来到北方,生活上就更不习惯。食堂经常做一种把玉米糁和大米掺在一起蒸的米饭,看起来黄白相间,同学们戏称为“蛋炒饭”。为了补给大家的伙食,朱康院长煞费苦心,每星期都能让大家吃一次鱼,还想方设法从第二机械工业部(后来的核工业部)、第七机械工业部(后来的航天部)要到一些羊肉,有一些同学身体浮肿了,朱院长还让食堂每天为“病号”学生每人准备一碗豆浆。
1963年毕业,我先是被分配到北京酒精厂,1964年被抽调到北京市“四清”工作队,一直到1966年底。那时候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北京酒精厂开启了“酶法制酒精”科研项目,我被抽去搞项目,直到1970年4月才调回北京轻院。
周老师1961年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毕业,1962年被分配到北京轻工业学院,成为机械系的一《轻工设计》等专业基础课,课时量大、教学任务重。我跟周老师1967年结婚,1968年我们的大儿子出生,由于工作忙,我们不得已把孩子送回上海,交给我妈妈抚养,等学校西迁前夕我们去上海接孩子的时候,他已经两岁多了,一见我们就叫“叔叔”“阿姨”,我听了心里真难受。
西迁咸阳:千里奔徙的奋斗长卷
1970年1月,中央发布一号通令,要求党政军高层、部分高校、科研机构、重要工厂等迅速疏散至三线地区,以防苏联突然袭击。轻工部皮革所搬到河南平顶山,发酵所搬到江西宜春,烟草所搬到河南南阳,北京轻院由于选址一直未定,所以搬的比较晚。当时我们住在月坛附近的轻工部大院,从1970年初到年底,大院晚上的灯光逐渐稀少,等11月北京轻院搬迁的时候,院子已经漆黑一片了。
周老师作为“先遣队”员,1970年8月底就到咸阳了,提前完成了建设食堂、澡堂、宿舍等基础设施的工作。食堂、宿舍都是比较简陋的,食堂由瓦工操作,几个青年教师负责打下手,砌炉灶、弄烟囱、搬东西,差不多到10月中旬建好。大家白天干活一身土没处洗澡,就在食堂的大锅里洗,细粮不够吃,经常吃所谓的“钢丝面”——米玉面做的杂粮饸络,硬得像钢丝一样,一盘饸络浇上醋就是一顿饭。
11月初,周老师回到北京,我们用了三天时间销了户口、买了一些东西、装箱、托运。学校给我们一人发了个大木箱,考虑到咸阳物资贫乏,我们把能带走的书籍、教案、粮食甚至猪油、酱油膏、蜂窝煤都装了进去。月底,我们一家三口从上海坐火车到咸阳。
安顿好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接从北京托运过来的学校资产,当时还没有招学生,从火车站搬运东西都是老师们搬运。不论几点,广播里一通知,全体教师都去火车站搬东西。虽然辛苦,但是大家人心齐,几十个车皮的物资,几千套桌椅板凳、那么多书籍、实验设备,一会儿一批,都是我们肩扛手搬过来的。
刚到咸阳那两年,日子虽然苦,但是大家一起吃苦,反而觉得很乐观。我们住在老8号楼,和林学翰老师家共住一套房,朱康院长第一批来咸阳,也住在这栋楼,一栋楼住了40多户人家,其他的老师都住在平房里。我们南方人要吃米,但是北方只有面粉,周老师骑自行车到渭河南边的村子,用面粉去换大米。
周老师总是对我说:“你看人家朱康院长、机械系主任曾广寿、教研室主任詹启贤他们,年纪比我们大那么多都能克服困难,我们年轻,应该向他们学习。”朱康院长真是处处做表率。当时的老楼里,垃圾是从楼道垃圾洞往下丢,每周每家轮值从一楼掏出来集中处理。朱康院长已经是正厅级9级岗,当时算是整个咸阳地区级别最高的干部了,可是他从不搞特殊,事事身先士卒,到了值日那天,总是一大早就掏垃圾、运垃圾,规规矩矩,一点也不偷懒,有次垃圾道堵住了,朱院长还自己动手去掏。70年代国家困难,为了补给生活,朱院长带着大家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,在彬县老虎沟农场种粮食、养牲口,解决了吃饭难题。
二次创业:锻铸辉煌的铮铮誓言
西迁咸阳以后,学校发酵专业就停办了。我没有了自己的专业,一下子迷茫起来,当时轻工部开始研发半导体收音机的计划,我被抽到可控硅研究项目组,负责制备无离子水,用于晶体清洗、氧化蚀刻等用途,一直干了两年多。
1973年初,栾慧斌院长找我谈话,他说轻工部皮革所挂帅,轻工部发酵所、中科院微生物所、上海皮革厂共同开发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,地点在上海重革厂,目标是采用酶技术来改进脱毛生产工艺。之前传统的制革脱毛常用硫化钠和石灰的混合液浸泡生皮,使毛发松动脱落,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硫化氢、氨气,非常不环保,皮革厂都臭得不得了,以酶技术脱毛机,能优化工艺、改善环境。我是学发酵的,对酶有研究基础,所以被选进组。
这一年,我跟着项目组先后在上海重革厂、上海酒精厂、上海益民皮革厂的实验室,先是选择菌种并扩大培养,最后到酶的制备。项目的核心技术是要选择一种能水解毛囊蛋白质的酶,把大分子的蛋白质链水解成小分子,水解完了以后,再在转鼓的外力下脱毛。这样一来,皮也脱的干净完整,毛也可以回收利用。我们项目组研制成功的酶取名叫“166中性蛋白酶”,因为试验了166次才最后成功。“166中性蛋白酶”的菌种最初从哪里来呢?组内的专家们想到老虎、狮子等大型纯肉食动物的消化功能好,其消化液中肯定含有非常多的蛋白酶,所以我们就去动物园找老虎和狮子的粪便,从中采集菌种,再用菌种来培养符合需要的蛋白酶。我们先后在黄牛、猪皮上都做了实验,脱毛效果很好。这个项目后来被命名为“制革用酶制剂新菌种-166蛋白酶的选育与应用”,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把生物技术应用到皮革领域,在1978年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,这是我们学校首次荣获的国家级科研奖项。
有了这次研究基础,1973年底回校后我就转到了皮革系。那时候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已经进校,潘津生教授让我教《皮革工艺》课。在北京轻院学习的时候,发酵专业和皮革专业的基础课是一起上的,到三年级才分班,所以我有一定的知识储备,但半路改行,我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,幸好在上海这段时间我在厂子里和皮革厂工人一起订实验方案、改进工艺并且亲手操作,所以改行带来的陌生感很快消失了,后来还教《工厂设计概论》。我深刻体会到,理论上只要通了,改行也快得很,相比那些科班出身却没有参与生产实践的教师,我对皮革的了解更深刻,而且生物工程和皮革一交叉,反而给了我更多启发和收获。后来我和李临生老师合作的“戊二醛鞣剂的研制和应用”获得中国轻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。
1980年代,可口可乐、健力宝等风靡市场,轻工部提出“社会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”的口号,全国轻工类高校都开始兴办食品专业。1981年底,校领导找我谈话,让我和田家乐老师、谢金玉老师一起重新筹办发酵、食品专业。1982年3月,我和田老师、谢老师开始四处考察,我们先后去了轻工部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、西北大学、无锡轻工业学院、天津轻工业学院。那段时间,轻工部在天津轻院成立了一个软饮料生产培训班,我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,还去广东健力宝厂、上海正广和汽水厂参观学习。回校以后,参与全国轻工院校合编的《软饮料工艺学》,并在学校成立了软饮料生产短训班,每个班四、五个月的时间,帮陕西饮料企业委培技术员。
1983年后,国家又开始兴办啤酒产业,我们又开始招收啤酒专业大专、函授学生。为了给学生打牢基础,我们把生物、化学领域的普通技术、专业技术、专业分析都教了,最后再讲生产工艺,培养得很扎实。汉斯啤酒厂的委培生每届都有20多人,还有华山啤酒厂、宝鸡啤酒厂、汉中啤酒厂,培养的学生供不应求。这段时间,郭志钧老师、欧阳琨老师从西农调入,贺小贤、周洁、刘金平等青年教师都陆续来到学校,我们的师资队伍初具规模。
1984年,咸阳南校区建成,校园里的雪松、女贞树都是我们一棵一棵栽的,大树在这片热土上扎了根,我们也在西北轻院扎了根;1985年,学校隆重庆祝第一个教师节,周老师获评学校优秀教师三等奖;1986年,学校成立食品工程系,设立发酵、食品两个专业;1988年,我和周老师双双评上副教授,周老师还担任了机械系副主任,开始参与组建工业设计专业(设艺学院前身);1996年,周老师评上教授。
寄语当前:追赶一流的鸿鹄之志
2001年,我即将退休,最后一堂课上,学生们送上热烈持久的掌声,我非常感动,也非常不舍。因为这份不舍,退休后我又担任了10年教学督导,经常乘坐校车来西安校区,看到美丽的校园、现代化的教学设备,想想我们在北京轻工业学院、西北轻工业学院时期的艰苦条件,不由得感慨万千。从青年时代起,我们这代人在艰难曲折中和祖国、和学校同甘共苦,我们与时代洪流的每一波春潮冷暖相知,我们与祖国母亲的每一跳脉搏同频共振,对学校新时代的建设者,我们有几句肺腑之言。
一是要爱校荣校,团结一心谋发展。宣传部的同志给我们带了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的报告,周老师和我都觉得很好,学校规划的发展战略高瞻远瞩、切实可行,我们相信只要全校教职工围绕所定的计划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必将实现“双一流”建设目标。我们的教师要立足学科特色,在“新轻工”建设上发力;我们的学生要扎扎实实学本领,在创新创业、实习实践中练就过硬能力;我们的干部职工要强化服务意识,为学校发展提供坚实保障。
二是在科研上要汇聚、投入资源干大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为了筹建发酵专业,我们去无锡轻院参观,回来很受打击。当我们的实验室还只有三角瓶、试管的时候,无锡轻院的实验室已经有先进的光谱仪、色谱仪。回到学校,我和贺小贤带着拮据的经费去西安采购仪器,为了省钱跟人家讨价还价,一个蒸馏器、一个烧杯都很珍惜,说白了还是因为我们资金不充裕。这几年我们去西安校区参观,看到先进的球差电镜,现代化的实验大楼,打心眼里高兴和自豪。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,我们要聚集资源干大事,才能把传统轻工学科干出新气象、新成果。
三是在人才培养要上保持“三实作风”的优势。我们轻工背景的专业,实践性都非常强,只在课堂、实验室是学不好的。我在皮革系任教的时候深有感触,我们的皮革专业实习特别多,认识实习、生产实习、毕业实习,有一年带着惠转瑜他们班去上海红光皮革厂实习,一去就是4个月,学生在工厂里摸爬滚打,学到非常多的知识,也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,后来分配到工作岗位上,领导同事都赞赏有加。“三创两迁”大学精神内涵中也包括了“求实创新、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”,我认为“实”和“新”都是在与科学前沿和生产一线的碰撞中体现的,在当前时代,企业才是应用研究与技术转化的主力军。所以我们要注重让学生增强动手能力,开阔科学视野。
回忆半生讲台生涯,往事历历在目,我们衷心希望学校越办越好,早日实现“复兴”蓝图!
(核稿:李萌 编辑:赵诚)